作为一个穷孩子,我为妈妈破旧的礼物感到羞耻现在我明白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和我每年都会做一些只需要微波炉加热的圣诞“饼干”。我们用微波炉烤,因为她成堆的购物袋和其他囤积的东西挡住了我们去烤箱的路。当我们在半夜烤完后,我妈妈会把我拖到警察局和消防站,在那里,睡眼惺忪的急救人员应门接受我们破旧的礼物。我觉得这太丢脸了,我几乎不敢直视他们的目光。
妈妈的欢呼掩盖了她的挣扎。由于离婚的打击,她强迫性地花掉了自己的工资。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公寓已经被碎石吞没了。
从我记事起,塔吉特百货(Target)的清仓区就一直是我妈妈的乐事,尤其是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抚养权争夺战之后,她成了单亲妈妈,背负着健康问题、债务和一个愤怒的青春期孩子。不久,老鼠在我们的公寓里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地板缩成了狭窄的小径。我们的床和厕所成了唯一可以坐的地方。14岁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寄养家庭。
一直以来,我妈妈在她的付出中发现了难以置信的快乐和意义。
她从她的灌木丛中割下紫丁香,放进Planters花生罐里,送给我学校的秘书。她主动提出在养父母的院子里种上自己花园里的花。我妈妈设法说服了我在县里任命的导师接受了这个提议,在她的房子里摆满了多年生植物。有研究表明,美国穷人是这个国家最慈善的人,但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的慷慨让我感到愤怒。
我接受了一些有钱人的观点,并责怪我的妈妈:如果她不再考虑别人,她就会有时间和精力来修复自己。我发誓绝不要像我妈妈那样,我把我的青春期奉献给了一个追求全a的人。
一个陌生人让我给她拍照。它救了我的命。
但当我开始在哈佛上大学时,我的许多同学都是慈善机构的创始人,他们的网站很漂亮,而且总是洗头发。在未来学生的周末,我和两个女孩走在一起,她们都在非洲创办了教育非营利组织。想起妈妈做的节日“饼干”,我羞愧难当。回馈社会让人感觉遥不可及,就像特权的真正标志。它需要一个公司的标志和一个晚会,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参加。同龄人的慷慨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贵人施恩”(Noblesse oblige),即认为精英应该善待地位低于他们的人的观点,在享有特权的“我们”和不那么幸运的“他们”之间制造了隔阂。在一项实验中,认为自己更富有的参与者缺乏同情心,更愿意分享。这与我在工人阶级社区看到的互助行为完全相反,互助行为的驱动力是一种“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也会去那里。”
研究表明,同情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是慷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平等的环境中,富人会变得更吝啬。随着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这种“同情差距”已经被证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我正在一家餐馆吃饭,一个男人递给我40年前的作业
在最好的情况下,给予提醒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弱点,但它经常被用来获得地位。在欧洲和北美,超过一半的最富有的捐赠者把钱捐给了教育事业(通常是他们的母校),捐给艺术和文化事业(通常是一些有声望的机构)的人略少。权力驱使下的慈善似乎比像我妈妈那样与强迫交织在一起的捐赠更糟糕。
我妈妈很慷慨,因为她明白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她知道给别人吃东西的不同——即使你给自己吃的是半融化的SlimFast巧克力棒。
在我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是那些在奋斗中帮助我最多的人。离开寄养家庭后,我依靠朋友的父母,他们让我睡在他们的沙发上,晚饭给我吃杯面。虽然我是一个独立的青少年,但在那些时刻,我并不感到孤独。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地拯救我,但我知道,对我的主人来说,分享他们所能分享的东西意味着什么——而且是出于同情而不是怜悯。
在我二十出头的那段时间里,我自己的捐赠也被恐惧所玷污。我害怕任何物质上的过剩会把我变成我妈妈,所以我经常去免费小图书馆和社区冰箱送孩子。虽然这些旅行缓解了我的焦虑,但囤积另一种资源——现金——却让我感到内疚。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回馈一个收留了我十几岁的收容所时,我惊讶于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好。
光靠慈善永远无法解决困扰我年轻时的问题,但写第一张支票让我意识到,像我妈妈一样,我可以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帮助别人,避免被忽视。
埃米·尼菲尔德是《接受》一书的作者,这本回忆录记录了她在寄养和无家可归期间的经历。201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她写过这段经历。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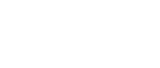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