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20多个家庭学校会议我在那里目睹的事情让我震惊

我是女孩赋权事业的创始人。我们制作了课程包,用历史上著名女性的故事来教导女孩们她们的价值和潜力。我是作家和研究员,我的商业伙伴B(也是我最喜欢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之一)是创意和营销专家。
我们合作得很好。当有分歧时,我们倾听,寻找共同点,一起解决问题。有时候,找到解决方案似乎是不可能的。有时解决方案会变得完美。
在大流行之前,我们与学校合作,提供我们的课程。政府关门后,我们失去了这些合作伙伴,但我们找到了家庭学校的支持者。这个社区全心全意地接纳了我们。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参加了20多次家庭学校会议。我们公司有很多支持和兴奋的客户。我们甚至得到了回头客,我们喜欢在这些活动中与他们重新联系。
然而,有一个派系对我们的存在感到刺痛。B和我试着把它刷掉,但即使是最小的碎片,如果不处理,也会引起感染。
一位母亲走进我们在密苏里州展厅的展位。“好吧,我女儿喜欢哈丽特·塔布曼。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她说。
我解释了我们的产品,我们如何利用历史上的女性来教育女孩们她们的价值和潜力。妈妈说:“但是它醒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不想教我的女儿什么是觉醒。”
我看了看我们的课程表。她们都是为平等而奋斗的女性。我对自己说,当然,它醒了。这个潜在的客户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我停下来,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在我的脑海里,我听到了《公主新娘》里的伊尼戈·蒙托亚:你一直在用这个词。我不认为这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我明白她认为她在问什么。她不想要任何自由、进步的东西,也不想要“雪花”写的东西。但她知道“醒了”不是坏事吗?
“你说‘醒了’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张开嘴。半句半句的话踉踉跄跄地乱蹦乱跳。新闻来源的一些谈话要点掉了出来。最后,她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再告诉我一遍你写了什么。”
在俄亥俄州,一位妈妈轻快地走进我们的摊位。
“哦,我的天哪,我喜欢这个。我要给我女朋友买这个!她告诉我。“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你教女权主义吗?”我的意思是,我相信平等,但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不想把它教给我的女儿。”
我采用了我在密苏里州使用的方法。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她。
“那么,你们教导女人比男人好吗?”
“不,我教导所有性别都是平等的,应该被平等对待。”
她买了三套。
我在德克萨斯州,我的家乡。一位母亲走进来,拿起一本日记,读到第一位女侦探凯特·沃恩的故事。
“你在哪里做研究?”她问道。我给了她几个网站。“很好,很好,”她说。
“那么,”她又开始说,“你有什么倾向?”
“斜?”我问。
“你倾向哪一边?”
“只是历史事实,”我告诉她。
“好吧。但是听着,我需要你为我做点事。”
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显然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了。
“写圣经人物,”她说。“我们需要这个。尤其是男人。”
我把头歪向一边。
“嗯,我们关注历史上真正的女性,”我说。
错误的答案。
“好吧,我得考虑一下。”
她松开我的手。友谊结束了。

我正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座里。这是一个漫长的早晨。突然,我感觉到一个人的存在。我转过身,慢慢地,进入我的视线,一个老人的脸向下滚动。下巴,鼻子,眼镜。
“你还要做更多吗?”他问道。
我忍住了他因咖啡味而做的鬼脸。
他抬头看了看一幅插图,上面突出了我们历史上的女性。我站起来,后退两步,把椅子挡在我们中间。
“是的,我们希望再增加两名女性。今年秋天,我们将接纳第一位亚裔美国女性进入陆军。然后我们将在2024年制作一部拉丁裔电影。”
“嗯,希望不是弗里达·卡罗,”他说。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回答。
“不,她不好,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告诉我。
“她做了很多好事。”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好,”他解释说。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我回答。
他走开了,我呼了一口气。我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屏住呼吸。
我还在南卡罗来纳。一对夫妇来到摊位前。他们昨天来过,我跟他妻子谈过了。昨天,她的丈夫保持沉默。今天他看到B,很兴奋。
“这里有个家伙,”他说。“他准备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在欢迎这对夫妇回来的时候,我侧目看着B。我和他的妻子聊了聊,她们走过来看了看我们的产品。
几分钟后,丈夫走向B。
“我妻子不知道铆工罗茜的故事,”他说。“我要告诉她,但我需要你核实我的情况。”
B朝我这边瞥了一眼。
“实际上,希瑟才是写传记的人。”
“是的,我知道,但是检查我,”他告诉B。
没有其他人在卡座里,所以丈夫站在中间。中心舞台。他张开双腿,微微弯曲膝盖,他的妻子在为表演做准备。
“好吧,他和我……他开始说。他伸出双臂,戏剧性地向B和他自己做手势,两人一排。“我们去打仗了。你和她——”他指了指我们两个女孩——“呆在家里,造飞机来支持我们。我们——”又一次挥动手臂来表示排——“用飞机赢得战争,回家。”
他得意地看着b:“是这样吗?”
我被这个十秒钟的二战重演搞糊涂了。我突然发出一阵尴尬的傻笑。B看着我,我耸耸肩。B独自和这个人在一起。
他清了清嗓子说:“嗯,还有更多的原因,但我想是的。”
这对夫妇购买了课程,并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开设一所合作学校。
回到德州,一个女人经过。她盯着摊位,又看了看我。她眼里含着泪水。
“这太神奇了。请给我一份所有的东西,”她对我说。
她确实每样东西都买一件。她感谢我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她低声说:“你在家庭学校会议上看不到这种类型的课程。相反,你看到的是那些类型的东西。”
B和我看着她指的地方。在旁边的摊位上,一家公司正在出售押韵的圣经故事书。他们的横幅上有一个卡通版的白色耶稣,他有六块腹肌,二头肌可以维持几天,手上有钉子洞。他周围都是棕色皮肤的人,鼻子又大又弯。
我们都惊呆了。后来,B和我想知道什么和耶路撒冷押韵。
德克萨斯州的另一个城市。一位妇女和她年长的母亲走进了电话亭。他们拿起产品,发表评论,但谁也不承认我。
一个人拿起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莎拉·格里姆格尔的故事。封面上写着"跟随你的心"
年轻的女人转向她的母亲,相当大声地说:“你知道前几天(插入女儿的名字)对我说了什么吗?”
“什么?她妈妈问。
“她说,在主日学校里,她学到你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只能听从上帝,因为你的心对你撒谎。”
那位年轻的女士终于看着我说:“连我女儿都懂。她才9岁。”
她把日记放回去,他们就离开了。我没告诉她只有女孩子的心才会说真话。

我们在佛罗里达。我走过一条过道,注意到一道红光,这是其他过道所没有的。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想到:这整个通道都是政治组织。这与教育无关——只是政治——每个摊位都有一些红色。
我经过一些写着“罗恩·德桑蒂斯世界”的牌子。B说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模仿迪士尼的字体。几个展位正在进行播客采访。我在手机上查看播客,发现每个播客都在传播阴谋论。
我经过另一个摊位,一男一女正在讨论持枪权……在一个家庭学校会议上。然后我经过一个“妈妈争取自由”的摊位。我的胃在滴水。
我们又到了密苏里州。我们卖了很多产品——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个母亲和儿子购买了我们的产品,这样他就可以了解萨卡加维亚。这让我很开心。
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欢迎所有男孩到_____展位参加俯卧撑比赛。”
所有年龄段的男孩都去摊位,围成一个圈。他们的头在中间,脚在外面。比赛开始了。有很多人大喊大叫。女孩们围成一圈观看。我想知道他们在看男孩们的时候在想什么。没有女生比赛。
我在加州。这是本赛季最后一次会议了。我又吐了一次,因为我担心会有更多随意的评论和粗鲁的问题。今天早上,我要向满屋子的人做报告。我正在讨论如何建立女孩的自信。我的演讲进行了20分钟,一位女士打断了我。
“你什么时候才能在这一切中谈论上帝?”她问道。
她的粗鲁使我反感。我深吸一口气,微笑着。
“你想让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我不能告诉你,”我回答。
另外两个女人起身离开了。
后来,一位女士回来道歉。她承认,从我的演讲中走出来不太像基督徒。有时我忘了我身边是基督徒——在这些会议上,“对别人做”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那天晚上,我终于告诉B我在会议开始前想吐了。他问我们是否需要停下来。我想答应你,但我做不到。
虽然呕吐是新鲜事物,但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关于B,有一点,他会听从我的指挥。不用我说,他就能得到双重标准。在内心深处,我们俩都没准备好被迫离开。所以,再一次,在喝酒的时候,我们想出了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引起冲突的地方的理由。
“我们在这些活动中赚了很多钱,”我说。从我嘴里出来的感觉很脏。B点了点头,又点了一杯。
他说:“你的事情正在改变话题。”“改变关于美丽文化的对话。改变我们如何培养有能力的女孩的话题。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改变一下关于女权主义的话题怎么样?”
他的眼神,表明他有一个疯狂的天才想法。
“如果我们真的开始谈论女权主义,而不是回避这个话题呢?”也许你举办的研讨会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权主义是好的。你可以成为公然教授女权主义的女人……在一个保守的家庭学校会议上。这是辉煌!”
我大笑起来,部分是好奇,部分是因为我觉得他疯了。
“我们会被取消的,”我告诉他。
“有充分的理由,”他回答说。
酒保端来两杯脏马提尼。
希瑟·斯塔克是一位企业主、播客主持人、公众演说家和女权主义作家。她的女孩赋权公司Grace & Grit通过历史女性的故事帮助女孩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她是《她的故事:一个滑稽而真诚的公司》一书的作者nversation一关于为什么美丽千里新事物应该是选择,而不是期望。”她和家人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帕德雷岛。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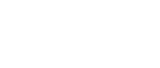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