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麻烦母亲”去世了,对我来说是个谜揭露她的故事改变了我的生活

12岁左右,我意识到我母亲有些“不对劲”,我知道这与酒精有关。
我可以走进一个房间,只要朝她的方向看一眼,就知道她是否喝了酒。有时,这些迹象很微妙——轻微眯起眼睛或夸张的手势——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其他时候,在场的人都能看出来她喝醉了。
回想起来,很难确定我母亲与酒精的关系是何时从社交变成依赖的。
在我童年早期的记忆中,我有一对慈爱的父母,他们对他们的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中间——永无止尽地负责。我们住在令人兴奋的地方。我在毛里塔尼亚度过了我生命的前两年。我的小弟弟出生在菲律宾。我们每三到四年就搬一次家,据同行们说,我母亲是“典型的外籍人士”。
然后,他们开始独自啜饮葡萄酒。作为一个终生的夜猫子,她的睡懒觉开始越来越像是一觉睡到天亮。她经常在聚会和其他活动中喝醉。“她今晚会规矩点吗?”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
不久之后,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与其说是由于冲突,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话。我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她的“问题”。我觉得我需要保护我们的家庭和她的名誉。
我渴望成为像我父亲一样,在联合国工作,努力工作,一心拯救世界的人道主义者。相反,我把她看作是一个不应该做什么的例子。我对她的评价是,她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她丈夫的工作要求她住在任何国家,包括那些政府不稳定、院子里藏着蝎子的国家。
***
一个沉浸在物质世界中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是遥不可及的。即使他们真的在场,即使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清醒,他们也不在那里。你无法完全接触到它们。有一种无法超越的情感距离。如果对方根本不承认有问题,那么你们之间就存在着谎言,这种不诚实掩盖了你们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手势。
从小到大,我母亲一直陪伴着我。她参加了所有的独奏会,唱诗班音乐会,话剧,垒球比赛。当我从学校回到家时,她在那里,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当我周末和朋友出去时,她熬夜等我。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正在经历一场缺席。我知道我生她的气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的愤怒隐藏着另一种感觉,一种类似于悲伤的感觉。我非常想念我活着的母亲。
虽然我最初拒绝她是出于愤怒,但也是出于自卫。把我拒之门外,感觉就像是她先拒绝了我。
***
我最终选择了一条与我父亲相似的职业道路。我曾为少数几个非政府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宣称要“结束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我试图揭露和讲述她们的故事。当我执着地追寻女性生活经历中不为人知的复杂故事时,我自己的母亲却日渐衰弱。
***
当我父亲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了31年后终于退休时,我的父母搬回了他们在佛蒙特州的家乡。那年夏天,我决定在他们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家中为他们举办一个退休派对。8月的一个清晨,客人们还没到几个小时,我就发现妈妈在我家的后门廊上,我在那里放了一块很大的拼贴板,上面贴着过去30年的照片。妈妈坐在野餐长凳上,脸离桌面只有几英寸,她凝视着自己的生活,永远与她嫁给的那个男人在一起,或者在他的背景中。
虽然严格来说是我父亲要退休了,但我确实想让这个派对是关于父母双方的。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我是否成功了。我仍然有偏见,把父亲放在人道主义的神坛上。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些畏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礼貌地朝她的方向点了点头。她答应了。带着微笑。
***
我母亲于2014年7月去世,享年63岁,这是她自我消除的最后一步。当她离开我们时,她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
之后的几年里,我继续学习专业课程,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为止。当时,我指出了一些外部因素是我离职的原因。但现在我明白,一旦我一直试图“拯救”的那个人离开了,我的动力也就消失了。
我决定——最终——去了解我的母亲帕姆,她在世的时候我是无法做到的。我要揭露她的故事。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揭开这层面纱,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问题。几十年来,很多认识并爱着帕姆的人——朋友、家人、前男友——都向我展示了这个独立、爱冒险的女孩的快照,然后是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女人。当我慢慢拼凑起她20岁出头搭便车穿越欧洲部分地区时的轶事、感伤的记忆和柯达照片时,我有幸瞥见了一种物质早已模糊的复杂人性。
我现在明白了帕姆是如何发现自己走上了她那一代许多人走过的道路——由于母亲、配偶和管理家庭的要求,她的选择越来越少。沉溺于酒精可能有助于麻木现实与那些失去的可能性之间的不一致。
我还发现了别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我母亲在德国教了几年英语。1974年,在给家乡一位朋友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最近购买的出行工具:一辆自行车。她说:“(这是)10速赛车的风格,让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我找到一张她骑这辆自行车的照片。它有一个亮黄色的车架,后轮上方悬挂着两个侧筐,其中一个挎着一个米黄色的挎包。她身体前倾,穿着一套不同寻常的骑行服装——裙子、黑色紧身衣和靴子——她面带微笑。

她当时的一个朋友记得,妈妈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她的公寓里,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背包里拿出啤酒瓶,让大家分享——这在当时对女性来说是不典型的行为。
在我25岁左右的一个夏天,我在喀麦隆的一个当地妇女商业合作社工作,我也把啤酒放在一个背包里——这让收银台的工作人员惊讶不已。我的交通方式也受到了质疑:在城里坐那些摩的安全吗?
在我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不像我母亲那样。到那时,她从自己的撤退中完全留下了另一个人——一个脆弱的人,一个依赖的人,一个似乎没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的人。
但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们是多么相似。在喀麦隆购买那些啤酒时,我以为自己是在追随父亲的职业脚步。我根本不知道我走在她的房间里。
***
我很难理解我为什么要和母亲保持距离,即使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而,现在,我似乎在做相反的事情:跨洲追寻她的故事。我戴着她的首饰,为纪念她而纹身,在我的梳妆台上放着她大学时代旅行的纪念品。我甚至用她16岁时养的那只狗的名字给我的狗取名。我正在尽我所能,穿越从她失去自我开始的那段距离。
我不能让我母亲复活,也不能回答剩下的所有问题。但我可以把生活注入她多年来淡化的故事中,在对她的新认识中,我能够重新找回自己身上体现她的那部分。我不再在生活中看到我母亲,但现在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她。
需要药物使用障碍或精神健康问题的帮助?在美国,拨打800-662-HELP(4357)获得SAMHSA全国帮助热线。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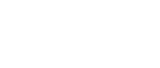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