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从悉尼的炎炎夏日来到了莫斯科的寒冬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定是11月底,也许是12月初。在出发前,刚好有时间挤进四节俄语课。
那是1991年的夏天,我即将开始一项后来被证明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最刺激的任务:为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ABC TV)派驻莫斯科,在那里我很快就会与受人尊敬的电台同事莫妮卡·阿塔德(Monica Attard)共事。
新年即将来临,我把悉尼夏天能提供的一切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海滩、海边游泳、烧烤、家庭聚会和告别,背景是刺耳的蝉鸣。
圣诞节期间,我一直在考虑该带些什么。我的衣柜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度过俄罗斯寒冷的冬天,在网上购物盛行之前的日子里,悉尼的商店在盛夏时节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即将离任的前任约翰·隆巴德(John Lombard)建议我效仿他的做法:在赫尔辛基稍作停留,买一件芬兰羽绒服(他向我保证),既保暖又耐穿。事实证明,这是我收到的最实用的建议。那件忠实的衣服让我度过了一切。很多次,当我和我的船员降落在另一个前苏联的贫瘠前哨时,那里有狭窄的床,破旧的毯子,几乎没有暖气,芬兰外套会兼做毯子和全能的被子。
1992年初,当我带着刚刚掌握的一点点俄语抵达莫斯科时,世界对俄罗斯仍然抱着玫瑰色的眼镜。前一个月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镇压了一场未遂政变,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
西方相信,强迫俄罗斯进行快速的经济改革,将把俄罗斯拉入其舒适的俱乐部。前苏联帝国各个地区内部和之间所有的种族和少数民族紧张关系都将神奇地消失。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对俄罗斯未来的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
不到两年后,情况恶化到叶利钦下令军队轰炸国家议会,以平息共产党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不太可能的联盟的叛乱。叛乱分子正在传递大部分民众的不满,对他们来说,混乱给他们带来了比前苏联领导下更多的困难和怨恨。就像森林大火不断从自己的余烬中重新点燃,前苏联的旧紧张局势也在燃烧: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阿布哈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冲突,以及乌克兰和莫斯科之间的第一次麻烦。
跟上这个过山车般的故事是无情的,令人兴奋的。1992年4月,在《先驱报》当时在莫斯科的传奇记者、已故的罗伯特·豪普特(Robert Haupt)的劝说下,我休了三个月来的第一天假,和他一起进行了一次不太可能的一日游。
豪普特以典型的浮华风格说服了两名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征用了一架大型直升机,飞到历史名城诺夫哥罗德(直线飞行约490公里)吃午饭。
船上有一群记者和一些无足轻重的外交官,还有一箱伏特加。这是一次长途旅行。那些厌倦了交换战争故事的人在后面打扑克。我和来访的英国医生兼医学作家约翰·科利(John Collee)攀谈起来,他碰巧坐在我面前。意外的惊喜。两年后,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1991年的夏天,突然进入了俄罗斯的冬天,确实改变了一切。
黛博拉·斯诺是一名狱警《先驱报》的撰稿人和前副主编。她曾两次获得沃克利奖,其中包括她在俄罗斯的报道她死了。1992年1月至1994年3月。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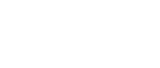


发表评论